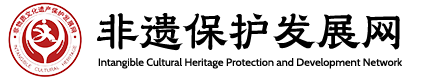非遗影像是用影像记录非遗、表现非遗、传播和传承非遗的文化实践活动,丰富多元的影像实践使其成为当今最为活跃的影像类型。走进异彩纷呈的非遗影像,从传统溯源入手,锚定基本定义和寻找相关论题域——与非遗保护的根本目标相一致,是解决理论创新的唯一路径和逻辑起点。
当下,影像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成为一种结构性、功能性的力量被贯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全过程。非遗影像的价值和功能不仅在于记录、建档、保存、研究、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具有对民族国家文化基因进行“编码”和“重组”的重大意义。这既是影像技术、功能和价值不断升级换代的结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文化双创”)在非遗保护领域中的生动实践和价值彰显。但与非遗影像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实践中的热度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因论题本身的交叉性和跨学科性,其往往被相关学科所忽视和冷落,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为此,本文将从传统、定义及论题域入手,试图做一些基础性的学术建构工作,以求教于各方。 学界与业界已习惯于把我国非遗工作的开端锚定在2001年5月18日。是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19个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现形式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昆曲。作为申遗专题片的《昆曲》当然也就成为我国非遗影像的肇始者。但显然,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形来看,我们对非遗影像的认识和了解却不能狭隘到仅与某一非遗项目联系在一起,更不能无视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现实本身。 如果我们以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规模化的非遗影像成果现象来看,在中国非遗影像的历史中,有这样五个大的脉络一直因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它们是:戏曲电影和戏曲电视;人类学纪录片;传统文化题材影视剧;传统节日晚会;民族民俗类摄影。下面,我们一并简单描述之。 (一)戏曲电影和戏曲电视 1905年5月28日,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以三国时期定军山之战老黄忠刀劈夏侯渊为主要内容的京剧《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戏曲电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的电影类型,其发展根深叶茂,其研究薪火相传。高小健在《中国戏曲电影史》中,从“初始实验阶段(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初步探索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阶段(1935—1955)、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1956—1963)、极端政治化阶段(1964—1975)、新戏曲繁盛阶段(1976—1988)、整体衰落阶段(1989 —现在)”等7个阶段对中国戏曲电影的发端、发展、巅峰时刻和整体衰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而诚如该文作者在对戏曲电影的整体衰落阶段的描述时所写到的那样:“电视直播、录像播出的各种演出和电影、戏曲频道的建立、专门为电视创作的戏曲电视剧等等抢占了戏曲电影的生存空间,戏曲电影前景黯淡。”戏曲电视一跃而成为广大戏迷朋友和普通观众的新宠。邵振奇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戏曲电视栏目历经萌芽期(1978—1987年)、发展期(1988—1995年)、繁荣期(1996—2003年)、转型重塑期(2004年至今)四个时期。从‘戏曲唱段,我播你看’的单一形式,到‘多元共荣,采撷众华’的繁华景象,戏曲电视栏目先后完成了专题化、板块化、综艺化、娱乐化、竞技化的发展过程,分众化、品牌化理念愈加深化,参与性日渐凸显,栏目形式及内容亦趋向多元。”当然,戏曲电影和戏曲电视仍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称谓,在其大概念下,还有许多更为细小的单元构成支撑着这一脉非遗影像体系,为保存和弘扬中华国粹而持续地发挥着自己特殊的贡献和作用。 (二)人类学纪录片 新近出版的朱靖江《故乡回望苍茫:中国影像民族志史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21)试图把中国民族志影像的历史拉长到20世纪之初由西方传教士为我们留下的珍贵影像片段上;同时,也试图把中国民族志影像的发祥版图扩展到中国的东南西北。这是民族影像志史家的一种判断和学术描画,也为我们寻找中国非遗影像的蛛丝马迹提供了另一种学术可能。然而,从目前国内学界较为公认的说法来看,带有一定的人类学自觉的非遗影像不外由这样三个传统构成:一是孙明经在四川拍摄的一系列国民教育纪录片中的非遗影像;二是庄学本在藏边地区和西北地区留下的大量涉及民俗及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三是1949年后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大调查而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以下简称“民纪片”)拍摄工作留下的部分非遗影像。2007年,四川大学梁现瑞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纪录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中,也较早涉及了这一话题。他把纪录片与非遗相连接,有意识地把非遗影像的历史放在了百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之中来考察,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00—1930年)、发展阶段(1949—1966年)、繁荣阶段(1978—至今)”。尽管该作者的分期太过粗疏,但其中提到“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进行独立拍摄的工作则开始于1933年5月初,中研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苗族、瑶族等地区考察时携带摄影机并拍摄了一部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这是我国人类学者首次将影像手段应用于田野调查,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滥觞之作”。这一传统也是我国影视人类学最正统的一脉,它与民纪片有较大的承传性。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百部史诗工程”和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工作等,它们构成了与非遗媒介纪录片之间最大的理论张力,而非遗媒介纪录片则以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地方台30分》持续10年的经营密不可分,它直接导致了中国纪录片整体性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亮相,甚至还以“舌尖体”的形式刷新了人们对纪录片的认知。自此,非遗媒介纪录片成为非遗影像中最具影响力和显示度的类型之一,而由它开启的台网合一,或者说在新媒体视野下非遗短视频的疯狂生长也再次成为非遗影像的流量担当。显然,这些非遗短视频所形成的新的视觉文化体系,又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影像田野。 (三)传统文化题材影视剧 非遗与影视剧的关系最早是以部分传统文化元素进入故事片开始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中就有“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影像,之后民国时期的《西厢记》《木兰从军》《混江龙李俊》《生死恨》等少量影片以及再之后港台部分神怪片、武侠片和寻根片中均有涉及民间文学、传统戏剧和民俗的故事片大量产生。新时期,一批代表中国电影最高成就的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作品《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问鼎世界,其中就因部分传统文化元素的进入而引起过激烈的讨论。对此,魏殿林曾指出:“强势的影视流行文化将使仪式等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空间日渐变小,后者在依附中逐渐失却了独特的价值内核而被流行的力量所消解。” 除了作为局部存在的非遗故事片之外,在我国故事片生产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类非遗故事片,即以非遗为题材展开的电影创作,这个主要由少数民族非遗故事片(《刘三姐》《阿诗玛》《尔玛的婚礼》《赛德克·巴莱》《草原上的搏克手》)发端而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非遗电影类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它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传统节日晚会 在笔者的写作过程中,以“节日晚会”为主题输入中国知网查询,仅得到52条研究成果的显现,但如果输入“春节晚会”(以下简称“春晚”),却得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据—— 9985条。这便是作为传统节日电视晚会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2007年,当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从2008年开始,我国将正式把除春节之外的另外3个传统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一并纳入法定节(假)日序列时,其所释放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被称作“假日经济”。从另一维度看,这何尝又不是中国民俗学家为现代化中国再次植入传统“中国性”所做努力的结果。以春晚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晚会是新时代非遗影像最耀眼的名片,从1983年到现在已经历了40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研究也较为充分,但却还缺乏基础性的历史梳理,这无疑是需要展开的新课题。它自身的变化情况,它与时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央视春晚与地方春晚、网络春晚的关系,春晚与其他传统节日晚会的关系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尤其是当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正以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出圈”之后所引起的热议,更令中国传统节日的媒介化建构成为一种更为普遍和富有强大引领性的“文化双创”新景观。 (五)民族民俗类摄影 在“非遗影像”的大语境下,“非遗摄影”拥有其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与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下面我们仅从中国摄影与非遗的关系来追溯其传统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中研院一众学者和庄学本、孙明经等影像工作者为首的中国本土摄影力量崛起,他们在考察调研与个人创作的过程中拍摄的田野影像和纪实摄影作品,较之同时期西方摄影者,不仅在系统性和学术性上更胜一筹,在主位视角的表达、反思性和伦理正义性、参与式观察的深度等方面亦有全面突破。 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伴随着民族识别与民族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一批以少数民族同胞为拍摄对象的影像民族志应运而生。它们出现在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代表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或发表在《民族画报》《人民画报》等大众媒体上,具有一定学术研究性质。这些影像在以影像方式留存“少数民族行将消失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来面貌”的同时,对各民族的节庆婚俗、民间艺术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技艺等今日所谓“非遗”的文化事象均有较为系统、全面的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在纪实摄影运动的蓬勃发展中,中国民族影像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和新闻宣传的束缚,开始倡导人文关怀,在艺术表现上大胆探索,亦有人尝试将社会学、民族学的理念方法贯彻到其创作中,也为该时期关涉非遗的摄影创作平添了反思的色彩。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持续推进、硕果累累,摄影艺术事业也可谓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摄影”与“非遗”作为一对关键词频频携手见诸于报端,以摄影为手段记录非遗、推广非遗已成为全社会之共识。虽然“非遗摄影”这一概念在学界尚有待探讨,但上述历史足以证明其明确的学术渊源及天然的学术合法性,并清晰地显现出中国非遗摄影百余年来的发展脉络。